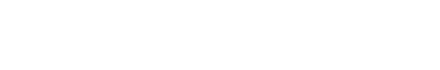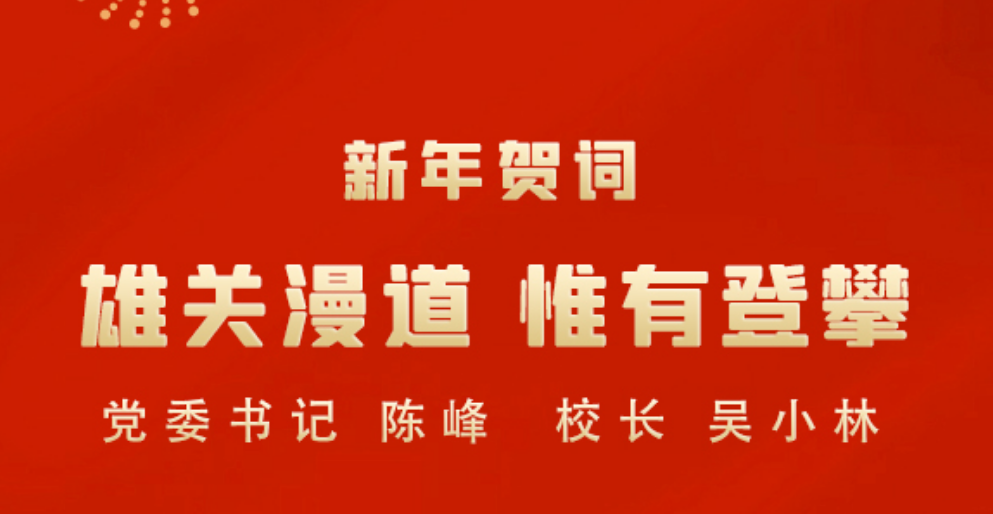崔立山:潛心治學是一種享受
發(fā)布時間:2013-03-21 | 來源:宣傳部 | 瀏覽量:
3月8日出版的最新一期《Science》,刊發(fā)了中國石油大學重質油國家重點實驗室、理學院材料科學與工程系崔立山教授研究組作為第一作者單位撰寫的論文“A Transforming Metal Nanocomposite with Large Elastic Strain,,Low Modulus and High Strength”(《一種超大彈性應變,、低彈性模量及高屈服強度的相變金屬納米復合材料》)。這是中國石油大學的名字第一次出現(xiàn)在這本世界頂級綜合類學術期刊上,。
能夠以第一作者單位在《Science》上發(fā)表學術論文,,對于任何一個學校,任何一名科研人員而言都值得驕傲,。然而在采訪崔立山教授及其研究團隊成員的過程中,,讓記者印象最深刻的恰恰是他們的平靜與謙和。這個由崔老師領銜,,三位青年教師和七位博士生組成的年輕的科研團隊,,面對成績所表現(xiàn)出的嚴謹、低調,,以及談及學術研究的認真,、熱情,有些不同尋常,,卻又自然而然,。
“做學問和做其他任何事情一樣,人的境界最重要,。”材料系主任陳長風教授的這句話,,也許真正道出了崔立山教授和他的團隊在潛心治學的路途中最強大的力量。
“不聰明,,就要更專注更認真”
崔立山常常自嘲為一個“笨人”,。他無數(shù)次問自己、問學生:“千人,、萬人,、幾十萬人做不出的成果,我們憑什么做成,?”答案是惟一的:無以憑借,,只能靠吃別人吃不了的苦,付出比千人,、萬人,、幾十萬人更大的努力,,才能有所突破。
他所謂的“笨”,,其實是20多年矢志不渝的專注,。1985年,崔立山碩士研究生在讀時,,就開始從事金屬相變材料的相關研究,。所謂相變,最為人熟悉的就是水在零攝氏度時會結成冰,,崔立山的主要研究內容是金屬由一種固態(tài)向另一種固態(tài)的相變,,這項研究在現(xiàn)實生活中應用最多的就是人們使用的金屬零部件通過固態(tài)相變提高性能。20多年過去了,,當絕大多數(shù)學者認為該領域已近“黃昏”而轉向其它領域時,,他依然還在堅持追尋相變領域與其他領域的結合點,期望在交叉融合中獲得突破,。他說:“沒有‘夕陽領域’,,只有‘夕陽人’。”正是這種執(zhí)著和不放棄,,促成了納米線這一新興領域與相變材料這一傳統(tǒng)領域的“姻緣”,,促成了這一篇《Science》論文的最終呈現(xiàn)。
他所謂的“笨”,,其實是只求把一件事情做好的心無旁騖,。2008年,崔立山的角色由中國石油大學研究生院負責人轉為材料科學與工程系一名普通教師,。他坦承自己不喜交際,,不愛應酬,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做研究,。在從事研究生院管理工作時,,雖然工作任務繁重,但只要有空余時間,,他就會思考一些學術問題,,他的工作筆記本前面是行政筆記,后面是密密麻麻的學術札記,。崔立山說:“與做行政相比,,我更適合做科研。但是做行政工作的經(jīng)歷,,讓我更能體會學校行政管理人員的不容易,,更滿足于自己的教學與科研工作,也更加感悟了做人做事的道理:踏踏實實做人,認認真真做事,,一定會贏得大家的認可,。”由學校機關回到實驗室,崔立山坐回“冷板凳”,,努力屏蔽外界的紛擾,,靜下心來,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教學與科研中,。
他所謂的“笨”,,其實是抓緊一切時間的勤奮。時間是崔立山看得非常重的財富,。他常說,,想法隨時隨地都可能產(chǎn)生,時間浪費了看不見,,擠出來就非常可觀,,可以用來做很多事情,。不過他也笑言自己有時候顯得不近情理:同事朋友到他辦公室,聊兩分鐘閑話兒他就開始不安,;朋友聚會吃飯他很難請動,,即使去了,話題也會很快在他的帶動下轉向科研教學,。在學生眼里,,崔老師是一位能吃苦的導師,愿意在實驗室工作,,節(jié)假日不休息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學生們開玩笑說:“崔老師這么拼命,我們哪里好意思偷懶,。”他的博士生,、此篇《Science》論文的第一作者郝世杰說,他在美國Argonne實驗室做實驗時,,經(jīng)常要和崔老師就一些數(shù)據(jù)和稿件進行討論,,崔老師最多隔一天就會把自己的意見回復給他,“從許多郵件的發(fā)送時間看得出,,老師常常要工作到深夜十二點后,,他的勤奮和高效迫使我不斷加快工作節(jié)奏,更高質量地完成實驗,,盡快出數(shù)據(jù),。”
“做學問真辛苦,也真快樂”
成功的背后一定有著不為人知的艱辛??稍诖蘖⑸胶退难芯繄F隊看來,,搞科研雖苦,沉浸其中就可以甘之如飴,。發(fā)自內心的熱愛支撐著這份堅持,,更贈予他們無窮的快樂。
2012年初,,研究組決定將已經(jīng)進行了三年的研究成果投稿給另一份世界頂級綜合類學術雜志《Nature》,。此時,青年教師姜大強電腦里的論文修改稿已有數(shù)十個版本,,它們完整地記錄了這項研究一步步成形,、一步步完善的艱難過程。直到1月22日,,農(nóng)歷春節(jié)的除夕,,修改還在繼續(xù)著。這一天,,崔立山,、郝世杰和姜大強分別在北京、美國和大連,,當人們都已沉浸在節(jié)日歡樂中的時候,,他們仨卻隔著萬水千山,還在通過電腦網(wǎng)絡視頻,,一個詞一個詞,、一個句子一個句子地反復討論和修改著文章。2月1日,,凝結了幾十個人數(shù)年心血的論文投遞了出去,。
然而,論文通過了《Nature》期刊的兩輪評審,,卻最終由于缺乏概念性的設計與猜想未得以刊登,。傾盡心力、滿懷信心卻遭遇挫折,,這對一個以年輕人為主的研究團隊而言無疑是一個不小的打擊,。采訪中,崔立山輕描淡寫地一語帶過了這次困境帶給他的壓力,。他像平常一樣,,一臉笑意地繼續(xù)鼓勵學生們不輕言放棄。郝世杰清楚記得當時那種幾乎要打垮自己的沮喪:實驗,,實驗,,無休無止的實驗,,幾年沒白沒黑的努力真的換不來想要的結果嗎?“那些天,,老師每天都會上網(wǎng)給我打氣,,強調我們研究中理論突破的意義,分析論文需要完善的地方,,讓我相信這次失敗不過是暫時的挫折,。”
此后,崔立山帶著研究組又開始了爬坡似的新一輪征程,,挑戰(zhàn)《Science》這個高峰,。參考《Nature》審稿人的意見,他不斷向國內外的專家學者請教,,繼續(xù)充實和豐富實驗結果,,進一步將理論概念與實驗所得、測試結果等結合起來,,把深層次概念的問題做得更為透徹,,更有說服力。2013年1月,,這篇又一次經(jīng)過了無數(shù)次討論和修改的只有短短幾頁的文章,,最終以開創(chuàng)性的原子尺度猜想、嶄新的設計理念,、巧妙的制備方法、超常的材料性能,、翔實的實驗數(shù)據(jù)征服了兩位審稿人,,順利通過了近乎苛刻的評審,敲開了《Science》的大門,,并受到同期《Science》期刊的專題評論,。
一個課題,歷時幾年,,過程一波三折,,結果不可預期,其中滋味,,倘不身處其中恐怕無以領會,。崔立山的學生王珊說起老師這幾年的兩次受傷,還是無法平靜,。材料制備實驗耗時耗力,,崔老師常常親力親為。有一次在實驗室軋板時,,一個飛濺而出的金屬片打在了他的腿上,,當時就血流如注,,可他只是作了些簡單處理,第二天又早早出現(xiàn)在實驗室里,。還有一次,,崔老師跟腱受傷斷裂,手術后醫(yī)生叮囑要少動靜養(yǎng),,可他還是忍不住常來實驗室,,直至跟腱再次斷裂,沒有辦法了才只好回家休養(yǎng),,但他還是每天通過網(wǎng)絡視頻與學生討論,。
不覺得枯燥辛苦嗎?崔立山說:“搞科研多享受啊,,做學術實在是太快樂了,,又有意思,又不受約束,,我太知足了,。”而他的這種幸福觀也實實在在影響著研究組的整個學術氣氛。
論文開始起草時,,正趕上姜大強的愛人生寶寶,。他一邊忙著寫稿,一邊照顧愛人和孩子,,過度的勞累使他的氣色很不好,。他的父母從東北來看他,見他一周七個晚上都在實驗室,,老人心疼了:“你們是啥單位,?咋總加班啊!”去年春節(jié),他在老家過年時除夕夜還在網(wǎng)上用視頻與崔立山,、郝世杰討論論文,,他母親急得說:“別做你們那個工作了,咱們回來放羊吧,!”有時崔立山也會覺得他太辛苦,,可他自己毫不在意。
博士生劉鎮(zhèn)洋說,,負責材料制備的姜江師兄很辛苦,,實驗室在地下,冬冷夏熱,,通風環(huán)境不好,,他經(jīng)常一呆就是一整天,感冒了很多次,,卻從不叫苦,。姜江聽了卻搖頭說:“哪有他們說的那么夸張,,實驗室挺好的,干起活來根本不覺得,。”
覺得苦,,是因為站在它的外面審視它、品評它,;當它與你融為一體時,,你感受到的只是心意相通的快樂。在一個未知領域的跋涉,,探索,,帶給崔立山團隊的,是真正的滿足與快樂,。
“學術交流是提高團隊水平的重要途徑”
在中國石油大學,,化學及化工、地質,、材料,、物理等基礎研究對微觀表征手段的依賴性較強。近幾年,,學校加大了對基礎學科,、支撐學科的建設力度,2008年投入1600萬元建成了能源材料微結構實驗室,,并將其作為重質油國家重點實驗室,、油氣資源與探測國家重點實驗室的重要組成部分。
作為能源材料與微結構材料實驗室的負責人,,崔立山自覺壓力很大,,“做好這個實驗室的工作,不僅要為師生服務好,,還要不斷提高自身的研究水平。”現(xiàn)在,,讓他感到欣慰的是,,實驗室已經(jīng)實現(xiàn)無休息日開放,每天上午8點到晚上22點都可以為來自校內外的師生提供服務,;而這篇在《Science》上刊出的論文,,也讓他對未來實驗室的科研工作充滿信心。
“做研究,,專注是根本,,苦練內功是關鍵,學術交流是重要途徑,。”崔立山雖不愛應酬,,但若遇到學術水平比自己高的專家,,他絕對是“主動出擊”,“厚起臉皮,,不怕拒絕”,,發(fā)郵件,打電話,,請專家來學校,,甚至為了與專家見一面專門趕到機場,想方設法向專家請教,,拿出自己的研究結果與專家討論,。
他說:“以這篇論文能夠被《Science》刊載為例,北京工業(yè)大學國家電鏡實驗室的韓曉東教授早在2009年9月就對我們的投稿指向提出了建議,;美國Argonne國家實驗室的任洋教授對同步輻射試驗與分析給予了指導,;麻省理工學院的李巨教授對初始稿件水平的提升提供了幫助;澳大利亞西澳大學的劉亦農(nóng)教授在論文文字表述方面提供了幫助,。所以說,,雖然論文主體學術思想與實驗結果出自于我們自己,但如果沒有后來與國內外著名學者的充分探討,,成果難以在《Science》期刊上這么快發(fā)表,。”
崔立山深知學術交流對于培養(yǎng)研究生的重要性。他常對學生說:“有些東西我也不懂,,但是我可以請來這個領域的專家教你們,。”早在擔任研究生院負責人時,他就積極推動研究生“聆聽大師,,與大師面對面”的高端交流活動,,請院士、專家到校為研究生開講座,,增長他們的見識,。回到研究組后,,他更是不惜投入,,常邀請專家到實驗室與學生們交流,同時支持學生通過各種方式到國內外學習,、實踐,。
他說:“我水平有限,但只要向高手學習,,我們團隊的水平就能不斷提升,。”
“我是帶著學生打獵的人”
在《Science》上發(fā)表論文,崔立山最高興的是鍛煉了研究隊伍,,“在高水平期刊上發(fā)表論文,,對于研究生樹立自信心,、提高眼界、提升認知水平的意義太大了,!”
崔立山一直強調:“這篇文章是研究生與教師集體攻關的結晶,。”2009年5月,當時還是本科生的于存在做畢業(yè)論文時發(fā)現(xiàn)了材料的優(yōu)異性能,;2009年10月,,碩士生劉明采用電解法制備出納米線;姜江將材料的優(yōu)異性能從95℃調整到室溫,;郝世杰利用同步輻射對材料性能機理進行表征,;劉鎮(zhèn)洋在北京工業(yè)大學做電鏡檢測;王珊,、史曉斌,、杜敏疏等分析了大量同步輻射數(shù)據(jù);姜大強老師在參與稿件起草與修改過程中付出了艱苦的努力,;楊峰老師在電鏡檢測方面進行了重要補充,;鄭雁軍老師在研究的宏觀布局方面給予了重要建議——在他心里,團隊中每個人的努力都如此重要,。姜江至今還清楚記得老師在團隊學術交流平臺上贊揚自己的那段話:“在材料制備過程中,,他付出了艱辛勞動,尤其是他不計較個人名利,、敢于冒風險,、為集體甘于奉獻的精神,為科研組師生所敬佩,。”姜江說:“我們的每一點付出,,每一點進步,老師都會看在眼里,。”
崔立山很在意學生,,喜歡學生,善于讓學生聯(lián)合攻關,。他把指導學生做研究形象地比喻為老獵手帶著年輕的獵人去打獵,,年輕獵手個個都是快槍手、神槍手,,但是他們還沒有找到獵物蹤跡的經(jīng)驗,,不知道到哪里能尋找到獵物,,在哪里守著能打到大獵物,,當老師的就要像個經(jīng)驗豐富的老獵人一樣,憑借自己的學識和判斷力,,幫助學生找到有價值的學術點,,并引導他們實現(xiàn)學術目標,。
論文的第一作者郝世杰是崔立山的博士生,從讀碩士時開始就跟隨崔立山學習,。他家庭經(jīng)濟條件不太好,,當年考研因為沒有被第一志愿錄取被調劑到中國石油大學材料系學習。入學時,,郝世杰找到還在研究生院當負責人的崔立山,,說自己因為錢不夠不能辦理學校入住手續(xù)。他走后崔立山心里很不是滋味,,當天晚上就找人打聽他的電話,,怕他無處安身,直到聽說他和在北京打工的姐姐在一起時才放心,。雖然郝世杰本科的專業(yè)方向與崔立山的研究領域不一致,,崔立山后來還是收下他做了自己的學生,幫他解決了不少困難,,并對這個能力與個性很強的小伙子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先后送他到北京工業(yè)大學國家電鏡實驗室和美國Argonne國家實驗室學習,開闊他的視野,,提升他的能力,,在他遇到困難、感到困惑時,,給予他無微不至的關心,。崔立山說:“將郝世杰作為文章第一作者,不僅是他參與了稿件起草,,完成了同步輻射實驗,,更為重要的是,他將在國家電鏡實驗室學習到的納米線知識帶回了科研組,,利用美國Argonne國家實驗室的同步輻射測試技術為許多博士生提供了幫助,。”
杜敏疏的英文水平在研究組里數(shù)一數(shù)二,對學術研究有著濃厚的興趣,。保送研究生到崔立山門下后,,這個很有主見的女孩子放棄了出國留學機會,留下來踏踏實實地跟崔老師學習,。她說,,她一直覺得自己很幸運,不僅跟崔老師學到了很多專業(yè)知識,,更感悟到了在做人做事方面老師的言傳身教,。有一次做課題時,她遇到了一個交叉學科的問題,因為崔老師對這個領域也并不了解,,所以她想去中科院物理所向相關領域的博士請教,。結果崔老師親自帶著她從昌平坐地鐵,直接找到了中科院物理所知名的教授,。杜敏疏說,,只要是學生需要,哪怕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老師也一定會盡全力幫助學生做到,。
崔立山很享受與學生一起討論學術問題時的民主氣氛,經(jīng)常將自己一些不太成熟的學術想法講給學生聽,,希望吸納學生們的不同意見來使想法進一步明晰,。他說:“探索,就是要先有猜想,,很多東西我就是沒完全想明白,,才找你們討論。”他還教導學生:“告訴你們一個小竅門,,你越坦承自己的不足,,別人就越愿意幫你!”許多到崔立山研究組交流過的國外專家都對團隊的學習能力和科研水平給予很高評價:“走了國內很多高校,,感到中國石油大學的學生對科研有興趣,,敢于提問題,有自信,,有想法,。”
學術無止境。經(jīng)過幾年的拼搏,,研究團隊不僅收獲了這篇論文,,而且可望探索出相變領域與催化、納米膜,、磁性,、超導等領域的交叉融合點,合作專家更是對他們未來的研究前景充滿了希望:“你們開拓的領域將是‘富礦區(qū)',!”
崔立山說,,面對這樣一個良好的開端,他感到自己的壓力似乎更大了,,“基礎研究的最終目標不是發(fā)表文章,,而是你的成果是否能起到引領作用。同時,,作為研究生指導教師,,我得加倍努力讓每位學生都能登到學術山頂,,感受‘一覽眾山小’的喜悅,并為學科建設和學校的發(fā)展貢獻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