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校地球科學學院青年教師龔承林博士和中國石油大學(北京)王英民教授,、意大利國家海洋和地球物理研究中心的Michele Rebesco博士(《Marine Geology》主編)和Stefano Salon博士,、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Ronald J. Steel教授合作完成的研究成果《How do turbidity flows interact with contour currents inunidirectionally migrating deep-water channels?》發(fā)表在地學領域頂級期刊《Geology》上(見下圖)。《Geology》具有重要的學術影響力,五年平均影響因子為5.047,,在“Web of Science引文數(shù)據(jù)庫”中地質(zhì)學領域連續(xù)11年排名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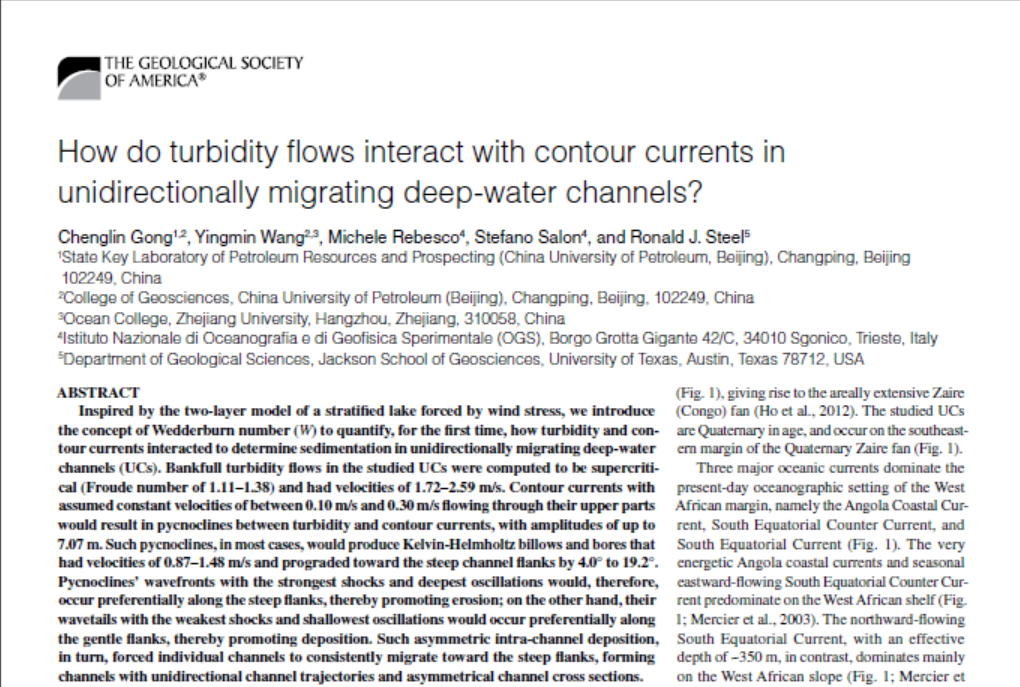
龔承林博士等人發(fā)表在《Geology》第46期的研究成果,。
“濁流與等深流交互作用”是深水大洋中除“重力流”和“底流”之外的第三大搬運沉積作用過程,,其沉積動力學機制是當今深水沉積學研究的前緣和薄弱環(huán)節(jié)。該研究以西非下剛果盆地發(fā)育的深水單向遷移水道為例(下圖A),,通過流體動力學計算揭示(理論模型見下圖B和C):當流向遷移水道遷移一側(cè)(陡岸)的等深流(邊界流速為10或30 cm/s)與遷移水道中的超臨界濁流(內(nèi)弗勞德數(shù)為1.11到1.38,,流速為1.72到2.59 m/s)交互作用時能夠形成一個“濁流與等深流密躍層”。該密躍層在遷移水道內(nèi)形成Kelvin-Helmholtz(K-H)波,,這些K-H波以2.53至4.15 m/s的速度和4.0°到19.2°的角度斜交水道的陡岸,,從而使得振動最劇烈、波長最大,、振幅最強的“K-H波頭部”出現(xiàn)在水道的陡岸,,以侵蝕作用為主,;而低速的“K-H波尾部”出現(xiàn)在水道的緩岸,以沉積作用為主,。由此可見,,濁流與等深流交互作用可在水道內(nèi)產(chǎn)生“陡岸侵蝕-緩岸沉積”的過程響應,從而驅(qū)動水道向陡坡一側(cè)持續(xù)穩(wěn)定地遷移疊加,,形成如下圖A所示的深水單向遷移水道,。

圖A:西非下剛果盆地發(fā)育的深水單向遷移水道典型剖面沉積構(gòu)成特征;圖B和C濁流與底流交互作用沉積動力學計算的剖面(圖B)和平面(圖C)理論模型,。
該研究揭示了除“重力流”和“底流”之外的第三大沉積作用過程(濁流與等深流交互作用)的沉積動力學機制,,豐富了深水沉積學基礎理論。審稿人對該文章給予了高度評價,,例如荷蘭烏特勒支大學的Joris Eggenhuisen教授認為該研究揭示了濁流與等深流交互作用的機制,,為濁流與等深流交互作用研究提供了沉積動力學模型(The paper truly treads new ground, which is a rare accomplishment in this day and age.I expect this paper to set the tone in exploring quantification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oceanography of contour currents and the sedimentology of turbidity currents.)。
該研究受到“油氣資源與探測國家重點實驗室杰出人才培育課題(PRP/indep-1-1701)”,、“中國石油大學(北京)優(yōu)秀青年學者科研啟動基金(2462017YJRC061)”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41372115)”的聯(lián)合資助,。

